
- P-ISSN 3022-0335
- E-ISSN 3058-2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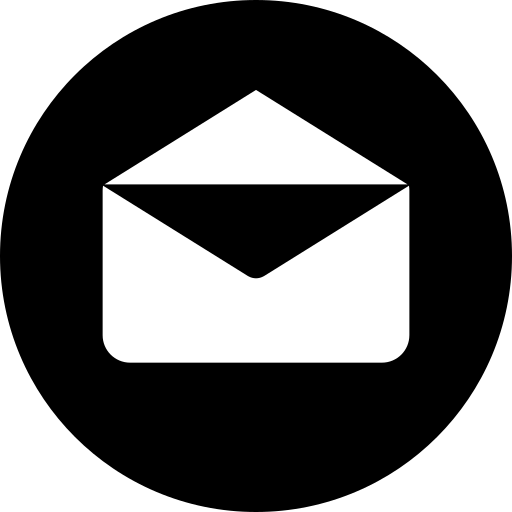
Buddhism believes that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is bound by karma and interdependent. Therefore, any cultural exchange in this world is a product of karmic harmony or disharmony and is additional interactive and bi-directional. During the nearly 700 years from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ibet in the 7th century to Buddhism's demise in India in the 13th century, it was common for Tibetan monks to seek enlightenment in India using gold as a material and materialized medium. This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direct reason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Tibet, but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In this article, the cause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using gold as a means to seek the dharma, the way in which "gold for dharma" was typically presented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 this practice on Ind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s are considered to explain the reasons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this historical phenomenon. Also explored is the cumulative role that using gold to seek the dharma played in Ind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This avenue of academic research posit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a novel perspective that examines mater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缘起共生、相互依存的,因此世间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都具有交互性和双向度。从公元七世纪佛教在藏地开始传播至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灭亡为止的近七百年间,藏地僧众以黄金作为物质媒介和物化媒介发起的去印度求法的活动,不仅是佛教传入藏地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印藏文化交流互鉴的代表。本文分别从黄金求法历史构境的形成缘由、黄金求法历史现象的呈现和黄金求法对印藏文化交流的传播及影响三个方面,来阐述黄金求法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印藏文化交流互鉴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以期从物质和文化的交互性、印藏文化交流的双向度这种新的角度来阐释佛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关键词: 黄金求法、佛教、印藏僧众、缘起共生、相互依存
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曾参访过桑耶寺、托林寺、扎什伦布寺、大昭市、甘丹寺、哲蚌寺等藏地著名寺院以及博达哈大佛塔、斯瓦扬布纳特寺等尼泊尔名寺,研究方向:藏传佛教,佛教史,汉藏文化交流,印藏文化交流。
佛教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Cebeta 2016a)。《大智度论》也说"一切法各各为因,各各为果,是名因果相"(Cebeta 2016b)。从佛教的观点来看,黄金求法也是诸多因缘和合的结果,下面分别就印度和藏地两个当事方的缘由加以阐释。
从印度方面来讲,黄金求法运动的产生首先是佛法的教义理念深深吸引藏地的僧众,其次是印度崇金的习俗以及印度佛教僧侣对黄金的崇尚和需求。
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他认为人生是无止尽的轮回组成,这种轮回的人生是痛苦的(苦谛),他分析了痛苦产生的原因(集谛),认为痛苦是可以断除的(灭谛),给出了灭苦的具体途径(道谛),其宗旨是为了出离生死轮回。针对当时印度社会中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佛教提出了众生平等的理念,其表现为任何僧众都可以用本民族的语言学法传法,都可以通过修行得到解脱,摆脱轮回苦海,这就为佛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它的戒律,其中最基本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和"六和敬"等。这些戒律归结一句话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青藏高原属高寒山地,这里空气稀薄,环璄恶劣,生存条件极差。生活在这里的藏地先民们自古就有敬畏大自然,崇拜自然界各种神灵的苯波信仰的传统,恶劣的自然环璄很容易使他们接授人生皆苦和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的戒律要求信众平等相处,和睦相待,互敬互爱,这些基本的佛教伦理和藏地先民朴素的伦理观相一致,它们为后来佛教传入藏地后与当地的苯波信仰经过几百年的相互抗争、接受和互融提供了先决条件。
印度人对黄金的喜爱由来已久,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的金胎颂中记载:"原初之时,独有金胎,生天地和太阳,它也是生主"(Mani 1979, 589)。印度人认为,世界是从黄金中诞生的,金胎创世说对印度的文化影响很大,对黄金的崇拜是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上世纪四十年代印度德信省发现了4500年前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遗址:"(人们)从废墟中收集到了数量惊人的黄金、白银、宝石和金银饰品,以及青铜器皿、金属器具和武器。大多数似乎来自那些被称为'富商的房子'"(Gordon 1972, 135)。考古发现佐证了印度在远古时期已流行黄金白银及金银饰品,可见印度人对黄金的痴迷是有历史渊源的。
我国东汉史书《汉书》中记载:"(罽宾国)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Ban n.d., Vol.96)。罽宾国是古印度的一个小国名称,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古印度产金银铜锡等金属,且已经使用黄金白银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
到了当代,印度仍然是目前全球民间持有黄金量巨多的国家之一,世界黄金协会(WGC)的Somasundaram PR表示,印度民间持有的黄金量可能在2.4万到2.5万吨之间,占据全球黄金储备量的14%。据《中国黄金报》报道:"2021年前三季度,印度贸易逆差超过1172亿美元,同比增速接近90%,而全年贸易逆差将接近1500亿美元。而在印度政府的贸易逆差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买了黄金"(Kong 2022, 5)。从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人对黄金的痴迷程度堪称世界第一。
印度崇金文明土壤中生活的佛教僧众自然也会受其影响,佛教经典中的创世说同样可见黄金的影子:
此器世界之形成,最初从空界中......形成水轮......由此生成七海底,其水搏击,上结成金,金地厚三十二万由旬,广量与水轮相等,周围即成三倍。其前风轮为娑婆界底,地水二轮为四洲须弥界底。黄金地轮之上,复降大雨,形成大海,被风钻击,精妙品聚集成须弥山,中品聚集成七金山,下品聚集成轮围山,杂品聚集成四洲等。其须弥山之体,东方为银,南方为琉璃,西方为红色水晶,北方为黄金,七金山为纯金构成,八洲山多为山边之铁构成。(Stag tshang rdzong pa 2017, 329-330)
多罗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年)的《印度佛教史》记载:"阿育王在他晚年时发愿向阿波兰多迦、迦湿弥罗、吐货罗等国僧众各奉献黄金一百俱胝"(Tāranātha 1988, 47)。阿育王统治时期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佛教那时已开始流行黄金供奉,由此可以推测出,黄金作为最为殊胜的供奉由来已久。
近代法国著名的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了古代藏地和印度僧侣间大幅度的财富流动现象,他的解释是吐蕃僧侣们从其印度上师那里继承了两大原则:一是弟子对上师的绝对服从,另一个是印度上师所有教授都要收取重金酬谢。"其原因之一肯定是某些密教仪规(尤其是曼陀罗)都需要作为祭品的大量珍贵物器。除此以外,还必需补充吐蕃僧侣们为追求经书和教法而遇到的大量困难"(Stein 2005, 144-145)。石泰安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佛教作为教派,离不开世俗的供养和物质的需求。
总之,作为人类传承久远的印度文明,自流传之初就深深烙上了黄金的印记,在其文明土壤中盛开的佛教文化之花,崇尚黄金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当藏地的僧侣满怀宗教的激情翻越千山万水来到印度求法时,他们同样入乡随俗地接受了印度文明中把黄金作为世俗的物质供奉和神圣的物化供奉的理念和习俗。
从松赞干布起心动念派吞米桑布扎(thon mi sambho dra)携带重金去印度求法和创造藏族文字翻译佛典开始,藏地就正式拉开了持续近七百年的黄金求法运动的序幕。下文就从藏地王室、民众对佛法的需求以及藏地蕴含黄金这三个方面来探析藏地僧众黄金求法的缘起因由。
在藏地正式归属元政府管辖之前,无论是吐蕃赞普时期或是西藏分裂时期,藏地一直都没有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王室和大臣之间的关系全靠相互之间誓盟来维持。每年一小盟,三载一大盟,誓盟期间需宰牲祭祀并指神为证。这种仅靠誓盟和指神为证的君臣关系并不可靠,一旦牵涉到大的利益冲突誓盟马上失效。王室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剧烈争斗几乎贯穿整个赞普时期和分裂时期的历史。利用佛教来加强对政权的控制是王室采取的手段之一,这在赤松德赞(742-797年)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赤松德赞继位时年纪尚幼,政权被信仰苯波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把控,他下令将释迦牟尼的佛像抛弃,将管理寺庙的和尚驱逐到汉地。赤松德赞长大后,为了反击玛尚为代表的诸大臣,他私下派人到汉地和印度学习佛法,又设计把尚玛活着关进了坟墓。在他在位期间,他请来印度佛教大学者寂护(Santaraksita, zhi ba 'tsho或译为静命)和莲花生(padma 'byung gnas)入藏传法,修建了桑耶寺,并在其中入驻了被称为"七试人"的吐蕃第一批出家僧人,请人翻译佛典等弘扬佛法的殊胜事迹。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吐蕃正式立足。
苯波信仰作为藏地的传统信仰,其势力集团在诸大臣和普通民众之间根深蒂固,无论是吐蕃王室或是后来的阿里王室都希望借助于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集团,能从精神上更好地控制大臣和普通民众,以期使神权和王权全部统一到自己手里,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
吐蕃王室时期,佛法主要是在王室和贵族之间传播,相比传统的苯波信仰,印度佛教不但给出了缘起共生、因果相连的解释并且给出了超脱生死轮回的修行方法。解决了基本物质需求的吐蕃王室和贵族选择佛法作为其精神支撑也就成为必然。
朗达玛(836-842年在位)灭佛被杀后,王室内部之间为争权发生了长期战争,最后导致了席卷整个吐蕃的平民起义,贵族阶层几乎被屠杀殆尽,藏地进入百年的黑暗时期。在灭佛事件中,僧人被杀或逃亡,幸存的僧人还俗民间,由此佛教下沉,以家庭为单位开始传播,这就让后弘期佛教入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近百年的战乱让普通民众深刻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他们苦难的人生需要寻找一种解脱的方式,由于当时的苯波信仰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没有教堂寺庙,没有僧侣,甚至没有完整的教义戒律,当时的它们并没有能力满足吐蕃民众的信仰需求,再加上求法回藏的译师们备受尊崇,于是携带黄金去印度求法就成为当时藏区人们最为时尚的精神追求。
黄金因其密度大、体积小,便于携带的特点,又因其在地球上含量稀少,自古以来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人们就其作为财富和货币的世俗性价值达成了共识。从地质角度考察,"地球上黄金产生的极盛时期是在震旦纪与寒武纪之间,即元古代和古生代之间"(Ren 2013, 4)。大约中新世中期,印度板块开始对欧亚板块进行挤压,青藏高原逐渐隆起。"最强烈的地壳运动是发生在中更新世之末并导致地形的大切割"(Li and et al. 1979, 613),大切割的结果是青藏高原形成数条深层断裂带,从元古地层至新生代都有。因元古地层蕴含丰富的黄金,故这些山脉经过数亿年的风化冰蚀,当部分山体崩碎,其中蕴含的黄金就会随水流一起冲刷到河流的某些地方沉积起来,成为砂金矿。
藏地自古就是黄金的产地,《汉藏史集》记载,达日年色王(约公元六世纪中期)在位之时,赤金日朗察已经"以木炭烧炼矿石得到金、银、铜、铁等"(Stag tshang rzong pa 2017, 119)。《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松赞干布第二次向唐太宗(599-649年)请婚,得到太宗的应允:"弄赞乃遣其相䘵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Liu n.d., 146)。可见唐朝时吐蕃已产大量的黄金。到了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探测技术的提高,藏地的黄金矿藏被探明的越来越多,仅以青海藏区为例:"目前在东昆化地域青海段已控明沟里、滩涧山、五龙沟、大场金矿、坑得弄舍金矿等大型矿区,累计探获333及以上黄金资源约达266吨,预测334黄金资源总量可达486吨,预测黄金资源总储量千吨以上"(Zhang 2015, 5)。以上的史料和数据都是藏地蕴含黄金的佐证。
黄金求法运动在藏地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吐蕃王室和阿里王室的大力赞助和极力推广以及僧地僧众不畏生死去印度求法的宗教激情,同时也离不开藏地蕴含黄金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诸多事物的因缘和合,自他相依,才促成了黄金求法活动在藏地持续近七百年的蓬勃发展。
黄金求法活动中,藏地僧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走出去"翻越喜马拉雅去印度求法,和"请进来"邀请古印度班智达到藏地弘法这两条求法路径,利用黄金这种物质媒介和物化媒介,在印藏僧众的共同努力下,把印度的佛教特别是密教传到藏地,它们与藏地原有的苯波信经过几百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下文分别就上述两条求法路径来呈现这种历史现象。
黄金求法的年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历史上记载的去印度求法的主要译师有大译师仁钦桑波(lo tsav ba rin chen bzang po, 958-1055年)、小译师雷必协饶(rma legs pa'i shes rab)、俄•洛丹喜饶(rgog blo idan shes rab, 1059-1109年)、卓弥•释迦益西(vbrgo 993-1074年)、洛扎•玛尔巴•却吉洛追(chos kyi blo gros 1012-1095年)、那错译师(nag tsho 1011-1064年)、贵•拉载(mgos lha btses)、热译师多吉扎(raw lo tsav ba rdo rje grags 1016-1196年)等等,这些先辈们不畏艰辛到印度求法,返藏后翻译了诸多的佛教经典,对佛法在藏地的弘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去印度学法的众多僧众一般分两类,一类由王室派遣,如大译师仁钦桑波等;另一类是自筹黄金,如热译师多杰扎等。
阿里古格王松额(965-1036年,srong nge,lha bla ma ye shes vod, 出家后名拉喇嘛益西沃)在位时,他从王族子弟中选了二十一个聪慧的少年,"再让他们携带大量黄金,去迎接当时印度最杰出、最有名的上师入藏"(Tucci 2009a, 25)。这二十一名年轻的求法者,从高寒的大雪山来到了湿热的印度,由于气候的不适,接连死去了十九人,最后只有仁钦桑波和雷必协饶经过长期学习后幸运地返回了故乡。他们二人在印度苦读经典,精通各种内外知识,被人们尊称为大译师仁钦桑波和小译师雷必协饶。青史记载:
大译师年轻时到克什米尔钻研过许多显密教典,具有大智慧而翻译出许多显密教法典籍,并广大讲说《般若波罗蜜多》及密续方面的教义,开示过许多灌顶和修法的做法。在藏区后弘期的密教比前弘期更为兴盛,这大概是大译师一人的恩德。大译师曾依止75位班智达而听受许多正法。(Yid bzong rtse gzhon nu dpal 2012, 76)
大译师三次去印度,他不仅学习佛法,同时也学习医术。"(仁钦桑波)在花了许多黄金向印度15位学者学习医学后,又带了100两黄金到克什米尔向医学家旃那达那学习《八支要义摄》和《达瓦希霍杰》等医术"(Ren 2003, 80)。仁钦桑波不仅在译经、传法和医术方面成绩斐然,他还在阿里三围修建了大量的寺庙,据图齐考证,史料中记载的仁钦桑波在阿里修建的二十一个寺庙都是真实存在的。
阿底峡尊者(jo bo rje, 982-1054年)于1042年入藏时仁钦桑波已经八十五岁。尊者带领大译师修行,尽管大译师已年届高龄,但他一心专修,最终取得殊胜成就。勿用置疑,大译师传奇的一生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都和黄金脱不开关系。
热译师多杰扎出生在聂纳朗地方,他一生中三进尼泊尔,二赴印度求法。他学成归藏后,一直传经授法,从事利于众生的殊胜事业,在实修方面,他同样成绩卓然,是同米拉日巴齐名的大修行者。
热译师传记中记载,他第一次去尼泊尔带了29两黄金,到尼泊尔后拜若巴(bha ro)大师为师,求学期间,他帮一尼泊尔巨商冶好病,获得500两黄金的酬谢,并把该黄金供奉给了巴若大师,大师传给他《金刚大威德要道》等法术。热译师第二次去尼泊尔带去了525两黄金,巴若大师传了他《吉祥大威德四字诛遣法》等法术。热译师第一次去印度拜那烂陀寺的大班智达门札朗巴(men dza gling pa)为师,临行前向班智达献了300两黄金作为酬谢。热译师回到藏地后广收学徒,讲经说法,三年后,他决定去印度迎请班智达门札朗巴到藏地弘法。
当大家听说热译师要去印度,所有学生都献了较多金子。大德王等君主、所有乡亲也献好多金子。总计得到金子十万两,热译师兄弟二人会同藏贡拉瓦师、尼泊尔译师,共4人前往。(R'a ye shes seng ges 2015, 183)1
上述藏文文献中记载的十万两黄金,真实性很难考证,也许是作者用的文学修辞手法,但不可否认,热译师此次去印度和尼泊尔必然是带去了大量的黄金。如此大量的黄金从哪里来呢?据《青史》记载:
当涅地举行桑波惹法会时,其弟子参加者有1200名教徒持《纳波继》教授,800密续者持同有同样的著述,总共2000弟子。热译师规定(讲授酬劳)每讲一次《作怖金刚续》为黄金一两(srang)。《纳波续》、《六面续》(gdong drug gi rgyud)、《胜乐续八种》(bde mchog rgyud brgyad)、《纳波六法》(nag povi chos drug)、《鲁耶巴》(luv yi pa)、《绛贝》(vjam dpal)、《二面》(zhal gnyis ma)等为黄金一钱(zo)。于是,他将上述著述作为著名的"金写佛经"。(Yid bzong rtse gzhon nu dpal 2012b, 344)
热译师只身前往尼泊尔印度求法,他不仅遵循当地的习俗供奉黄金给上师,当他学成归藏,也把黄金供师的习俗从印度带回了西藏。不同于其它译师们潜规则接收弟子黄金供奉的方式,热译师直接规定了讲授酬劳的标准,使黄金求法这种印度习俗在藏地得以合法化开了先河。热译师的弟子众多,他收到的供奉财物难以计数,利用这些财物,他重修了桑耶寺,供奉了108次法会,给多人寺院的僧人做物质供养和供献《经藏》等等众多利益众生的事业。佛教讲因果相依,热译师的一生成就和黄金供奉有脱不开的因果关联。
来藏地弘法的班智达大部分都是高僧大德,他们很多人进藏弘法主要不是为了黄金供奉,更多是为了信仰的热忱。下文分别就对藏传佛教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个人物寂护大师、莲花生大师和阿底峡尊者的事迹简单加以阐述。
前文谈过赤松德赞幼年即位,政权被苯波大臣把控,他为了控制政权,派塞囊(sba gsal snang)从尼泊尔把寂护大师迎请到王宫,大师在龙促宫讲佛法四个月,因发生瘟疫和荒年,信仰苯波的人们纷纷议论是赞普奉行佛法的报应,要求把寂护大师赶走。赞普只好奉上黄金把寂护大师送走,大师临走前推荐莲花生大师,认为他法力高强,可以降伏藏地众多本地神灵。后来赞普撑权后,他和大臣商议重新信仰佛法,于是派人去尼泊尔请莲花生大师,"而大师受护法神的劝请,在此之前已对身前往吐蕃,到达芒域时与迎请的使者相遇,大师接受了使臣奉献的黄金。"(Stag tshang rdzong pa 2017, 94)赴藏途中,莲花生大师先后降伏了永宁地母十二尊女神、念青唐古拉山神、龙王等众多神灵,让他们立誓守护正法。莲花生大师正式把吐蕃的本地神灵纳入到了佛教的体系,这是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开始,也是藏地民众接受佛教的重要原因之一。
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修建了桑耶寺。寺院建成后,赞普送给他们大量的黄金并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随后两位大师组织给吐蕃七青年授比丘戒,吐蕃的寺院开始有僧人入驻,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正式立足。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以桑耶寺为基地教授佛法,翻译佛典,为佛教传入藏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两位大师进藏是以弘扬佛法为目的,但是藏王派人携带黄金来迎请以及以黄金作为供奉以示尊重也是他们进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年拉喇嘛益西沃为了寻找迎请印度班智达进藏的黄金,被外道的国王捕获。外道国王要求阿里王提供与其身体等重的黄金才释放他。当时的阿里王绛曲沃(lha btsun byang chub vod)收集到了与拉喇嘛身体等重的黄金,仅缺少头部重量的黄金,但外道国王仍不放人。拉喇嘛觉得自己已经年迈,既使被赎回也为弘扬佛法做不了太大的贡献,就让人捎信给绛曲沃,让他把黄金用在请阿底峡尊者等大班智达进藏和弘扬佛法上面。拉喇嘛以身殉法后,绛曲沃为了完成其遗愿,派那措译师为代表去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
那措译师到印度后在甲•尊珠僧格(rgya brtson vgrus seng ge)带领下来到阿底峡尊者座前:"并供献上一整块黄金为主的许多黄金堆在曼札上"(Yid bzong rtse gzhon nu dpal 2012, 230)并向尊者详细叙述了吐蕃地方的情形。阿底峡尊者被拉喇嘛以身死殉法的精神所感动,也痛惜当时藏地佛法的乱象,继后:
阿底峡尊者启问本尊及金刚座获得成就之瑜伽母(是否应该前往吐蕃),本尊和空行母者对他说:"尊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到藏,那样对佛教将会有利,特别是将能使优波塞得到利益。但是,你的寿命将会因此而减少20岁。"尊者想:"只要对佛法和众生有利,减寿又有何妨?"(Yid bzong rtse gzhon nu dpal 2012, 231)
历经波折,阿底峡尊最终得以抵达阿里,绛曲沃将阿里三围的百姓全部招集起来,迎请尊者到他驻锡的托林寺,"奉献上黄金600两,做为请他宣讲一年佛法的献礼,并安排许多人受持斋戒、使很多人发菩提心"(Sba gsal snang 1990, 75)。阿底峡尊者在藏地弘法十二年,最后在聂唐圆寂,他把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都奉献给了藏地。尊者在藏地讲经译书,把戒律和密宗修行系统化,提倡三士道和业果的学说,规范了修行的次递。"一般传说认为正法的余烬是打康下部复燃的。但是,佛法的无欺教诫和无误讲传,实在只有尊者阿底峡一个余烬复燃而矣"(Sba gsal snang 1990, 75)。
据《布顿佛教史》记载,藏地携带黄金去印度求法学成归来且留有译作的著名译师有吞米桑布扎、仁钦桑波、那错、卓弥等共计192人。来藏地弘法且留有译作的古印度班智达有寂护、莲花生、阿底峡、巴尔加巴拉(shes rab skyong)等共计93位。在那个群星灿烂人才倍出的年代,印藏两地的僧众们在跨越喜马拉雅群山的共有的意义空间下,在延续六百多年的时间长河中,把佛教的经、律、论以及传承等通过黄金求法活动传至中华藏地,它们和藏地原有的苯波信仰经过几百年的相互吸收融合而形成了独具物色的藏传佛教,现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黄金求法活动在印藏两地僧众近七百年的努力下,把印度的佛教特别是密宗的火种翻越大雪山在青藏高原逐渐蔓延开来,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传播都具有交互性和双向度,黄金求法作为一种佛教传播的文化现象,同样具有交互性和双向度的特质,下文分别就印度和藏地两个向度分别加以阐释。
黄金求法运动延续了六百多年,没有谁知道在这段时间内到底有多少黄金从藏地流到了印度。藏地的僧众们携带黄金去印度求法,无论他们是否学到了心心念念的法术,当黄金花完时,他们就不得不返回故乡。被请到藏地弘法的印度班智达们,当他们收到藏地信徒供奉的黄金后,一般会派人把黄金送回印度并供奉给其原本所在的寺庙,但也有一些大班智达和瑜伽师到藏地只为弘法不为黄金。但总的来说,黄金求法运动中的黄金除了极少部分以贸易的方式回流藏地外,绝大部分都被留在了印度。滞留在印度的黄金随着社会的更迭变幻,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而逐渐流转到社会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因黄金的延展性和柔软性,它可以被做成任何的型状,又因其抗腐蚀性和不易分解性,故从藏地流入到印度的黄金虽然历经风云,但总重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它就象一只看不见的手,默默地推动着整个印度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直到千年后的今天,这些黄金仍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金求法结束五百年后,作为古印度之一的尼泊尔仍然有从藏地进口黄金的传统。发表于1857年的尼泊尔英国侨民霍德森(B.H.Hodgson)的行商日记中,记载了1830-1831年尼泊尔进口藏地的黄金的具体数字。详细资料如下图。
图表1. 1830-1831年尼泊尔进口西藏黄金数量统计表(Rn.Lucette Boulonis 1999, 102)
| 黄金级别 | 单价 尼币/托拉 | 重量(托拉) | 总金额 (尼币) | 备注 |
| 1级黄金 | 24 | 833.33 | 20,000 | - |
| 2级黄金 | 22 | 4,090.91 | 90,000 | - |
| 3级黄金 | 20 | 3,000.00 | 60,000 | - |
| 4级黄金 | 18 | 2,500.00 | 45,000 | - |
| 5级黄金 | 13–17 | 1,000.00 | 15,000 | 单价取中间值 15尼币/托拉 |
上表统计资料显示,1830-1831年西藏出口到尼泊尔的黄金总量是11,424.24托拉,约为133.25公斤。印度自古是黄金的消费大国,即使黄金求法已随着佛教在印度的消亡而停止,属于古印度地区的尼泊尔、印度人对藏地黄金的需求的习俗却保留了下来,藏地的黄金成了维系古印度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可获缺的物质基础。
史学家们一般把1203年伊斯兰入侵者烧毁恒河岸边的超岩寺(Vi-kramaśila)作为佛教在印度灭亡的标志。事实上,超岩寺被毁后,佛教仍然在印度残存了很长时间。十三世纪中期,藏地的一个僧人恰译师曲吉贝(Cha lo Tsa ba Chos rje dpal)到印度朝圣求学时,他记载当时很多寺院只剩下残垣断壁,也有部分寺院还有少数僧侣,金刚座是他特意去朝拜的圣地:"曲吉贝称,院里摆放着西藏'吹囊'('Phrul-snan)寺释迦牟尼的空宝座,受人膜拜,一盏长明灯悬挂其前面。印度和尼泊尔人总是说,在西藏,只要人们看一眼释迦牟尼的面容,人们就可免于沉沦地狱"(Cha lo tsa ba chos rje dpal 2013, 55)。 吹囊寺就是拉萨的大昭寺。曲吉贝到印度朝圣时,可以说黄金求法活动几近结束,没有谁知道,以前安立在拉萨大昭市的释迦牟尼的空宝座是在什么年代、由什么人运到了印度。也没人说得清从何时开始,作为佛教故乡的印度尼泊尔人开始把朝圣的目光从印度转向了雪域高原。
随着13世纪伊斯兰的入侵,因为战争的原因,无数的典籍被焚烧,幸免遇难的高僧们四散逃匿。又因新的统治阶层的政治打压,作为印度文化璀璨的明珠---佛教渐渐在印度消亡。幸运的是,经过近七百年的黄金求法运动,佛教在印度消亡之前,无数的佛学经典和传承特别是密宗已尽数转移到了西藏,避免了它们惨遭灭亡的命运。中华藏地接受了这份人类文明的遗产,它们通过与藏地的苯波文化相互融合吸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至今仍在雪域高原熠熠生辉。由于印度没有记载历史的习惯,黄金求法中藏地僧众们留下来的传记和著作,现在均成为研究古印度历史文化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为印度人民重新回溯和研究自己民族的这段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黄金求法活动跨越时间长、范围广,又因藏地僧众向印度上师学法需黄金供奉的原因,一个人可以跟据自己的意愿向不同的上师学习不同的法术,同时一个老师也可以把同一法术传给不同的学生,这就形成了佛教在藏地传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总体来说,佛教一开始在藏地的传承是无序的,到了后弘期,阿底峡尊者入藏后,他整顿戒律,规范了修行的次递,结束了藏地佛教的修行方法的乱象。尊者圆寂后,他的弟子仲敦巴(vbrom rgyal bavi vbyung gnas, 1005-1064年)遵照师嘱修建了热振寺,组建了僧团,开始讲经说法。仲敦巴的弟子博朵瓦(po to ba)积级授徒,主要教授《道炬论》(lam gyi sgrol ma)和噶当六论。"'噶当'(教授)这一名称,据说也是在博朵瓦时代中普遍传颂开的"(Yid bzong rtse gzhon nu dpal 2012, 249)。噶当派成立后,在藏区广收门徒,积级传法,后来噶当派弟子仲喀巴(tsong kha pa 1537-1419年)大师对宗教进行改革,他吸收了噶当派的精神,再加上自己对显密经论的理解造诣,形成了以实践和修证为纲领的新的教派体系格鲁派。原噶当派的僧人和寺庙也大都归属了格鲁派。
阿底峡的弟子们组建僧团的同时,其它的许多译师也开始行动,其中宁玛派据称是藏地最古老的一个教派,其传承来自莲花生大师,因在八、九世纪的时候,赞普推崇显宗,密宗的传承是单传且秘传的,到十一世纪"三素尔"的出现后,他们开始建立寺庙,形成了宁玛派,"大圆满"是该派重要的教法传承。萨迦派认为他们的传承可以追溯到赤松德赞时"七试人"之一的昆•鲁亦旺波松('khon klu'i dbang po srung)。他们这一派最开始是家庭传承,属于宁玛派。到了贡却杰波(dkon mchog rgyal po 1034-1102 年)时,他师从卓弥译师,于1073年在萨迦地方建立了萨迦寺,从此形成了萨迦派,"道果教授"是其主要的密法传承。
噶举派的祖师是玛尔巴大师,他曾师从卓弥译师学习语言,印度最著名的大师那若巴(na ro pa)是他的上师,他也曾听阿底峡尊者讲法,是当时著名的密宗大师。噶举为口传之意,这些密法主要是靠师长口耳相传,因此这个派别被称为噶举派。另外还有源于印度实证苦修僧人丹巴桑结(dam jpa snangs rgyas?-1117年)传下的两个派别希解派和觉域派。藏地最名的佛学大师布顿仁钦朱(buf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年)传承的夏鲁派等等。
宇妥•云丹贡波(gyu thog rnying ma yon tan mgon po, 708-835年),从小表现出了卓越的医学天赋,深得赞普赤松德赞的喜受,赞普提供许多黄金,派人把印度、唐朝、尼泊尔、波斯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医师请到吐蕃教导宇妥•云丹贡波。为了完善本民族的医学,宇妥•云丹贡波携带黄金前后三次共计九年八个月去印度学习。后来他在印度、汉地等多国医学的基础上,结合藏地传统医学,撰写了《四部医典》,奠定了藏医学的基础。他的十三世孙宇妥•萨玛云丹贡波(gyu thog yon ta na mgon po gsar ma,1126-1202年)曾先后六次去印度求学,其最著名的成就是对《四部医典》时行了注疏、补充和完善,形成了目前藏医学界最权威的经典《四部医典》。
天文历算是推算星宿运动和天气季节变化的一门学科。文成公主入藏时把占卜历算法带到了藏地。西藏的天文历算除了受汉地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时轮经》的影响。公元1027年吉觉•达尾峨色(gyi jo)第一次翻译了时轮经,藏地从此年(第一饶迥火兔年)开始使用饶迥纪年。
赤松德赞时让寂护和莲花生主持修建桑耶寺,莲花生大师进藏时带了一个建寺的匠人。据说桑耶寺是依照印度阿丹达布日寺修建的,顶层是印度木质结构风格;中层是汉地砖瓦结构风格;底层是吐蕃石头结构风格。里面的佛像是赤松德赞按照吐蕃人的形象建造的,桑耶寺是汉印藏三民族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整个藏地分布着许多佛塔,塔的形制多样,"藏地广为流传的图像学论著也是以印度制订的工巧论为底本,其中规定了建筑师、塑画师绘制、塑造、模制和描画各种图像时所必须遵循的规则"(Tucci 2009b, 5)。
藏地的僧众不仅把佛法请到藏地,同时也引进了古印度的壁画等艺术表达。现存藏地主要的壁画有东嘎壁画、皮央石窟壁画、扎塘寺壁画、托林寺壁画、古格王城壁画、白居寺十万佛塔壁画等。另外,藏地的佛教雕像、文学作品、修行法器等许多方面都打上了印度文化的烙印。
黄金求法活动作为印藏僧众之间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代表,因其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而对印藏两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年后的今日,当我们通过搜索古文本、文化收藏以及历史遗存来探究这种文化现象时,黄金求法活动作为中印两种文明交融实证现象已跨越了空间和距离的限制延伸到了时间的场域。黄金求法活动的介入,改变了印藏社会原有的社会体系,它们与原本的体系互鉴互融,经过一系列的重组和变迁,演化成新的属于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
佛教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相续、缘起共生的;同样,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因缘合和而成,都具有交互性和双向度。缘起于公元七世纪的黄金求法活动,在印藏僧众共同的努力下,通过近七百年践行发展,不仅把印度的佛教特别是密宗完整地传播到了藏地,而且把与佛教相关的医学、天文、历算、建筑、艺术等传入雪域高原。这些印度文化的结晶,经过近千年与藏地原有的苯波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现今独具特色的中华藏地文化。作为求法运动中最重要的物质媒介和物化媒介的黄金,则随着印藏僧众的求法和弘法的行程,被大量的从藏地转移到印度,为印度整个社会文明的运行和发展起到了坚定的物质基础的作用。在黄金求法活动结束后,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也反向对印度的信仰产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具有明显藏地特色的转山文化,直到今日,每年都有一些来自印度的不同信众到阿里的冈底斯山转山朝拜。
黄金求法活动中参与的两个主体方,当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达的古印度和刚刚摆脱蒙昧状态的雪域高原,在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中表现为:文明形态可以不同但其精神价值是相等的。正是因其精神价值平等和被尊重,印藏僧侣才有可能在共有的意义空间下使双方的文明得以交流融汇和发展。现今的世界正如一张"因陀罗网",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均为构成这张巨网的点和线,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佛教众生平等理念下践行的黄金求法活动为"因陀罗网"中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学共鉴、共创和谐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向。
[1] 补充藏文原文:de nas bla ma rgya gar du 'byon pa kun gyis thos nas/slob ma thams cad kyis 'bul ba'ang gser mang du phul/lha btsun sngon mo la sogs pa'i btsad po dang /yul mi thams cad kyis kyang /gser mang du phul te/khyon bsdoms gser srang 'bum byung ba bsnams nas bla ma sgu mchen gnyis/gtsang gong ra ba'i slob dpon/bal po lo tsa ba ste dpon slob bzhi byon/
Childe, Gordon 1972 "A surprising wealth of ornaments of gol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and faience, of vessels of beaten copper and of metal implements and weapons, has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ruins. Most appear to come from the houses ascribed to 'rich merchants'". In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First published 1942. Revised edition 1954.
Tucci, Giuseppe 2009a Indo-Tibetica Volume 2 of Brahma Buddha Land---Renqin Sangbo and the Revival of Tibetan Buddhism Around 1000 AD, translated by Wei Zhengzhong and Saer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图齐(意),《梵天佛地第二卷---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魏正中、萨尔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Tucci, Giuseppe 2009b Indo-Tibetica Volume 1 of Pagodas and Scratches in Northwest India and Western Xizang---On Tibetan Religious Art and Its Significance, translated by Wei Zhengzhong and Saer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图齐(意),《梵天佛地第一卷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塔和擦擦试论藏族宗教艺术及其意义》,魏正中、萨尔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